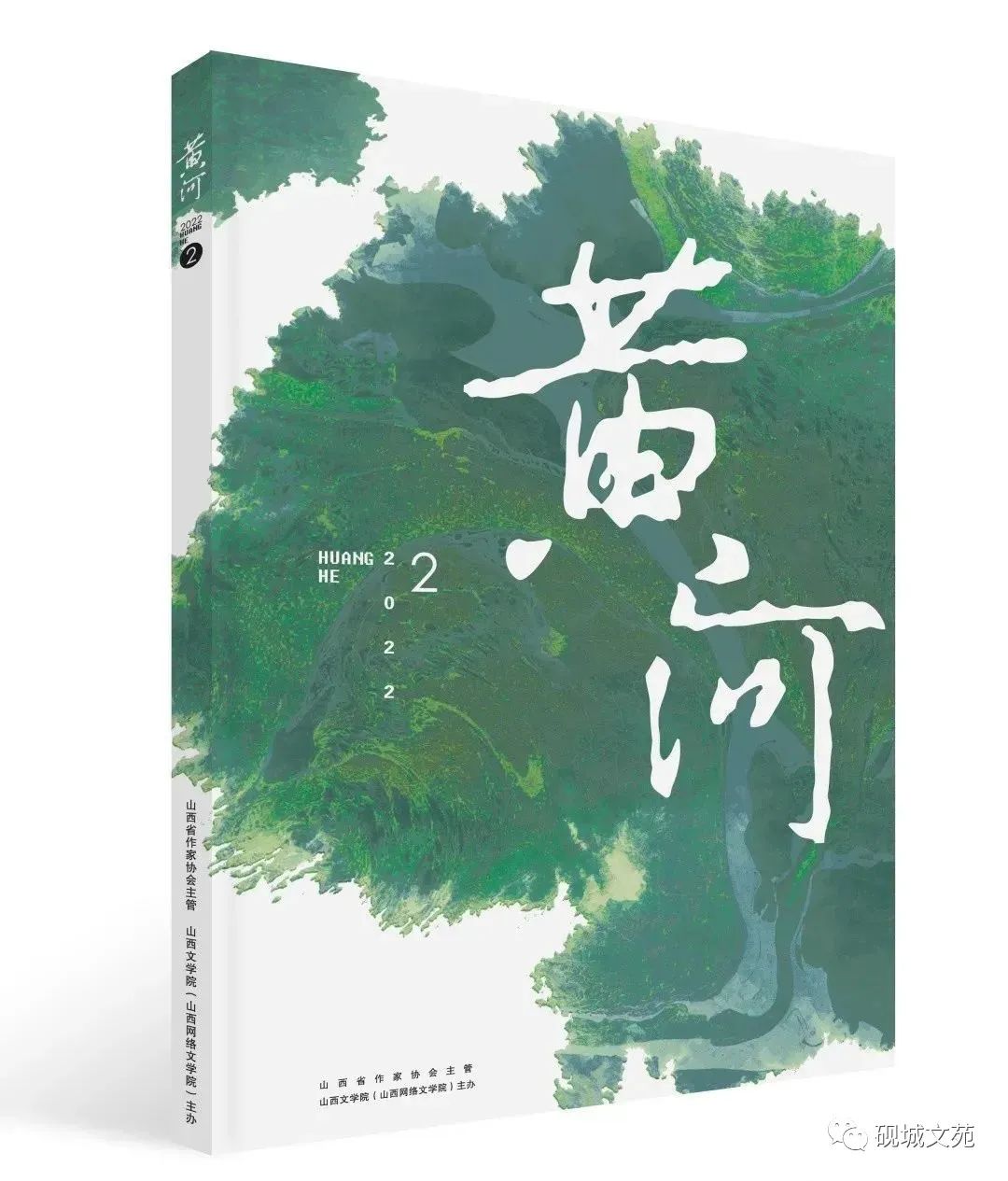

本文原載于《黃河》文學雜志2022年第1期和2022年第2期�。
二
舊寨村��,位于五寨八十里丁字平川的腹部�,全村350多戶,1100多人����,6000多畝耕地。從人口來講是全縣絕對的一流大村��,從生產(chǎn)條件和生活條件來講也應是全縣絕對的一流大村�����。
舊寨,一聽這名字�����,就有一種神秘感��,就會讓人聯(lián)想起舊兵器時代的一些軍事活動來�����。詞典上講����,寨乃防守用的柵欄,引申為舊時駐兵的營地�。舊寨這個村子,舊時屯沒屯過兵����,無從考證,但1977年駐扎過一個冬天農(nóng)水建設大會戰(zhàn)的民工連隊���,則是千真萬確的�����。
也可能是因了這個神秘的名字�����,那天在去舊寨的路上��,我的腦子里老是回旋著唐代大詩人杜甫的《兵車行》�。
看著我們這一行拉著行裝、草料�����、糧食的平車����,聽著驢蹄子在柏油路上踏出來的串串清脆而有節(jié)奏的聲響����,我的腦子里總在一遍一遍地背誦“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其實���,眼前的情景與這首千古絕唱驢頭不對馬嘴,哪有什么馬蕭蕭��,哪有什么走相送��,哪有什么咸陽橋�����,可明知不搭界��,還硬是要胡亂糾扯�。人這顆腦袋,真是有點兒稀奇古怪�����。
五十里路�����,走得人困驢乏��,等到了舊寨村����,已是中午時分��。
在打前站的貴生指引下����,我們很快在村子的西頭找到了將要入住的兩個院落����。
一個是楊氏院落,五間大正房���,院子頗為寬大�。一問才知道�����,這家主人是某公社剛剛退休的干部�����。這五間大正房中���,西面三間住著房東的兒子一家����,東面兩間的一堂一屋供我們作伙房和宿舍����。院子的西南角有一大溜小房子作驢們的草房和圈舍。這個院子就是我們這個排未來幾個月多功能的宿營地����,比我們想象中的場所強出了許多。
另一個院落的主人姓李�����,院子不算大���,典型的農(nóng)家小戶��,但收拾得利利索索�����,房東從三間正房中拿出一間來給我們當宿舍用�����。
安頓下來���,大家一齊動手����,先喂牲口��,再做飯吃����。
約莫下午三點來鐘,我剛放下碗筷����,就聽得院墻外有人呼喊:“徐家村的帶隊,趕快去連部開會�,快去,不得有誤�����?!?/p>
我一路小跑到了連部,見那房子的聽會席上已經(jīng)坐滿了人��。我找了個拐角旮旯勉強坐下來��,環(huán)視一周����,不免慌亂起來,原來其他村子都很守規(guī)矩�����,來的人不是支書便是主任�,只有我這么一個另類。那天我們村的支部書記倒是說過��,他要就其帶隊的特殊情況給公社領導作一專題匯報����,可鬼才知道他匯報過沒有。我心想����,怕是拉下糊糊了,說不定我這一來便會遭到發(fā)落����。
不大一會�,公社領導們便進來了���,他們在對面的條桌前依次坐好�����。還是官場上那一套����,主任主持���,書記講話�����。因為之前工程上的任務已經(jīng)明確����,所以書記講的和主任強調(diào)的就一件事��,那就是連隊的組織性紀律性問題��。要求我們所有人員發(fā)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雖不穿軍裝但要有個軍人的樣子���,講文明,講禮貌���,講衛(wèi)生��,和房東搞好關(guān)系����,和整個駐地搞好關(guān)系�����。不能打架斗毆�����,不能胡作非為�,不能發(fā)生任何有損于連隊形象的問題,尤其是離家在外���,要把那些火燒火燎的光棍后生們給看緊了��,千萬不能讓他們干出跳墻頭之類的事來����,云云。
在整個會議期間�,我像做錯了事的孩子,一直低著頭�,假裝作筆記,生怕把話題攬過來��,被領導當場開涮�����。
開完會��,我掉頭就往外走�����。不想還是被公社的馬鳴宏書記給發(fā)現(xiàn)了����,他把犀利的目光看過來,大聲吼道:“徐家村的小徐��,你等一下,還有事�,別著急走?!?/p>
他這么一吼,我的心情反倒平靜了許多�。我心想����,能有啥事?無非是說我沒資格帶隊吧��,其實我又不稀罕這個差事��,這又不是我爭來的或搶來的�,而是村子里的那幾個老頭子連哄帶騙,說年輕人該上就上�����,說這是個八輩子都等不來的機會����,說出去只有好處沒有賴處,說出去還可以得到鍛煉�����,硬把這營生給我碼駕在了身上。如果公社領導不認可����,那好說,只要有個干脆話�,我可以馬上拍屁股走人。
可是���,非常令我意外����,馬鳴宏書記不僅沒有解除我的帶隊職務�����,還狠狠地提拔了我一家伙�����。
他笑容滿面地對我講:“小徐����,是這么個事�����,按照指揮部的安排��,每個連隊都得成立一個宣傳小組�,給縣廣播站和指揮部的《戰(zhàn)地快報》提供動態(tài)和新聞稿件�����,以反映本連隊大會戰(zhàn)熱火朝天的戰(zhàn)斗景象���、改天換地的精神風貌、敢叫日月?lián)Q新天的英模事跡�����。動態(tài)倒是好鬧���,讓公社的干部們每天往上反映就是了��,可新聞稿件�,就需要專業(yè)水平了。你知道�,咱們公社小,這方面的人才少�,我們覺得還就是你能干得了這種差事。這是一個復雜勞動���,馬克思認為�,復雜勞動等于倍加的簡單勞動�����。也就是說在相同時間內(nèi)���,復雜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要比簡單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會高出很多�?!?/p>
因為馬鳴宏書記是省委黨校畢業(yè)的高材生,又當過若干年縣里的理論教員����,所以在講話中,經(jīng)常會時不時的秀兩句理論����。
他大概也感覺到了此時秀理論有點多余,于是微微一笑重回正題:“咱們連宣傳小組的組長是公社團委書記侯新文同志,這你熟悉�����,上下級嘛����!你給咱當上副組長,協(xié)助他把這個工作搞起來��。另外你在咱們連隊還要細心一點����,看誰還能寫達了兩句,也給咱組織進來����,共同完成這個任務��。具體的宣傳任務����,你去見見侯新文同志,好好商量商量�����,最好是搞個計劃出來,也有個目標和遵循�����。當然�����,你這是兼職����,希望你兩頭兼顧,既把排里的工作抓好�,又把宣傳上的事情做好。這種兼顧�����,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可能更有利于你的新聞寫作�����,因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又是認識的動力�����,還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實踐出真知就是這個意思�����,知行合一則從另一個角度強調(diào)了實踐的重要性��,有道是主觀必須見之于客觀���,認識必須統(tǒng)一于實踐�?!?/p>
說著說著,一不小心他又拐到了理論上��。
我早已知道��,馬鳴宏書記的理論水平非同一般�����。我也多次聆聽過他帶有濃厚理論色彩的講話�����。然而����,如此近距離聽他秀理論還是第一次。
我總覺得��,他的思維��,仿佛只有在理論的藍天下才會振翅翱翔����。
馬鳴宏書記的一番話,說得我熱血沸騰���。我一個村子里的泥腿子�,居然受到了公社領導如此這般的重用����,你說我咋能不激動萬分?咋能不受寵若驚���?我努力壓制著激烈的心跳��,給馬鳴宏書記表態(tài)道:“沒問題����,請書記放心,我會在火熱的生活中升華認識�,在偉大的實踐中淬煉思想,努力寫出具有時代特點和有家國情懷的作品���,以此來報答組織的關(guān)心和領導的厚愛���。”
我心想����,你秀我也秀,只不過��,秀的風格不同而已�����。此時的我����,很是開心。
緊接著我見了侯新文書記��,并按照馬鳴宏書記的安排我們一起擬訂了山道彎連隊的宣傳報道計劃���。其中最核心的內(nèi)容是�����,每周要給指揮部和縣廣播站提供兩篇以上的新聞稿件���。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個計劃����,竟把自己牢牢地綁在了大會戰(zhàn)的戰(zhàn)車上,以至于在真正改變命運的歷史機遇突然到來的時候��,也失去了騰閃挪移的空間��,這可能就是人們常說的作繭自縛吧�����。這是后話。
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我最初寫新聞那些事兒。1973年1月����,高中畢業(yè),回到村上�����,泥里出水里進����,覺得很不是滋味。在公社醫(yī)院工作的本家繼道二爹對我說�����,有志者事竟成�,總得尋一條出路,萬不可就此沉淪�����。我心想,有上層戶這頂帽子壓在頭上���,出氣都困難,還談什么出路���?有一天��,下鄉(xiāng)干部方紅霞給我支了一招���,她對我說,你那么聰明���,又有文化基礎����,何不試著寫些東西��,我有個親戚就是靠著寫作吃上公家飯的�����,后來竟然還當上了領導干部��,這條路也許能幫助你沖破成分的束縛。她的話給了我信心�,于是我開始學習學作。在煤油燈下�����,不顧一天的勞累����,半夜半夜地折騰,寫詩歌��,寫散文����,寫小說,寫新聞稿件�����,啥都寫�����,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可半年過去了���,寫下東西寄出去就泥牛入海了���。正在十字路口彷徨時,縣廣播站總算播了一篇我的稿件�。雖然文字不長�,但這個遲來的愛對我無疑是一個莫大的鼓勵。后來似乎把牌耍順了�����。我不停地寫�,廣播站不停地播,幾乎是百發(fā)百中�����。再往后縣文化館的《山花》也開始用我的詩歌了�,又算是碰開了一扇門。那年縣上把我評為模范通訊員���,還組織我們到大寨參觀了一回�����,真的感覺很牛逼���。這樣��,在那個山道彎公社的狹小天地里�����,漸漸就有了一點兒名氣�。包括公社有了材料��,也常常會請我回去捉刀代筆�。

來到舊寨的第二天,我們便正式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大會戰(zhàn)之中�。連隊給我們下達的任務是,每天每輛平車要往工地上運送兩立方沙子�。我們測算過,以每輛平車的最大載荷0.25立方來計算���,理論上需要跑夠八趟才行����。但事實上,除了路上的拋灑損耗����,以及車子的輪流檢修外,在工地上的平車子每天少說也得跑夠十趟以上�����,否則要想完成任務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里�,我們再換個角度���,來看看拉一天沙的里程情況。按平均運距1.5公里(這是當時官方給出的數(shù)字)計���,跑10趟總里程就是30公里���。30公里是什么概念?再加上一鍬一鍬的裝卸��,再加上有一半是負重前行�����,有過勞動經(jīng)驗的人們都能想到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勞動強度。
還有�,拉沙子的艱難程度遠不止這些。我們知道�����,沙子的比重是比較大的�����。我曾查過有關(guān)資料���,沙子的比重在1.47—2.9之間��,因其密度不同�,比重的范圍也頗大�����。這里我們?nèi)∫粋€中間數(shù)字好了���。假使五寨河的沙子比重為2��,那么拉一車沙子剛好在半噸左右��。當然��,半噸重�,在一般的平路上,驢子是完全可以獨立完成拉車動作的�����?��?墒瞧鸫a有三分之一的路程不是這樣���,比如在松軟的河槽�����、高低不平的耕地���、比較陡峭的土坡�����,如果沒有趕車人的幫助��,僅靠驢子的一己之力����,是斷然無法駛動車子的。
有鑒于此��,我們在每輛車子的左側(cè)都系了一根粗大結(jié)實的環(huán)形麻繩或皮繩���,隨時準備把腦袋伸進去�����,與驢并肩作戰(zhàn)�����。
其動作要令大抵是:將右手搭于驢的脖頸上���,凝神屏息,把身體也躬成驢那個樣子�����,然后大喝一聲,像田徑場上的百米運動員�����,旦等發(fā)令槍一響����,就鉚足勁兒沖刺。
當然�,這不是人和驢的賽跑,而是人和驢的合作�����。我們的合作����,無需言語上的溝通,只需步調(diào)上的一致�。
倘若遇見了驢子偷懶或耍賴�����,比方聽到號令���,看上去它是在邁勁兒�����,實則是在作表面文章���。用力倒是不假�����,可它的用力只表現(xiàn)在了蹄或腿上��,而沒有傳導到整個身體尤其是肩膀部位�,這就是一種典型的不配合和欠揍行為����。碰到這種情形,就給它兩鞭子�。
我們發(fā)現(xiàn),驢也有好驢賴驢之分�。
好驢類似于良駒,它有自己的品格和情操�����,有自己的臉面與自尊,盡管眼角經(jīng)常滾落著一顆又一顆委屈的淚珠�����,但它們顧大局����,識大體,牢記使命�,固守本分,任勞任怨��,無私奉獻�,不用揚鞭自奮蹄,平車不缷只管拉����。
賴驢則剛好相反,能偷懶就偷懶���,能耍奸就耍奸���,能抗拒就抗拒����,還經(jīng)常好耍個驢脾氣��,好尥個驢蹶子�����,只有挨了重重的鞭子�,感到了鉆心刺骨的疼痛����,才會縱身一躍,全力以赴�,被迫去履行本該由自個兒履行的職責。
但����,好驢是大多數(shù),賴驢是極少數(shù)����。我們絕不可以偏概全,認為所有驢都是被人鄙視的畜牲����。
我有時候真的很想為驢們鳴個不平���。我們清楚,在農(nóng)事活動中�����,驢一點也不比牛做的貢獻小��?��?扇藗儏s把所有的褒獎和贊美給了牛��,而把所有的貶損和辱罵都送了驢����。甚至在評判人的好壞優(yōu)劣時也少不了拿牛和驢說事��,比如在捧人敬人抬舉人的時候�,會用老黃牛、孺子牛��、墾荒牛等來作比喻���;而在損人咒人辱罵人的時候����,會用老灰驢�、野叫驢、雜種驢等來冠名���。我覺得��,如此對待牛�,牛當然高興����;可如此對待驢,驢一定會非常憤怒��。在此��,我強烈呼吁��,人類社會既要仁者愛牛���,又要仁者愛驢��。在對待牛與驢的問題上����,要力求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
一天又一天�,就這么個過法。早上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出現(xiàn)在了工地,傍晚在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才能結(jié)束一天的戰(zhàn)斗。當然�����,中午還是要有個吃飯和喘息的時間�,否則不僅人支撐不下來,驢也支撐不下來�����。
晚上從工地上回來��,還有一攤子營生等待著我們?nèi)プ觥?/p>
說實在話,此時的我們��,已經(jīng)是非常疲憊了�。我們多想趕快吃點晚飯,進入到休息狀態(tài)���??墒遣荒?��,我們吃了,我們睡了��,驢怎么辦����?此時的驢也許比我們更加疲憊,它們無非是不會說話不會表達不會抱怨罷了�����,我們無論如何都得先把驢子安頓好了��,再去考慮我們自己�。人應該是有良知的動物�。
平心而論���,出門在外��,驢就是我們的最大的幫手和最大依靠��。我們只有全心全意地照顧好它們����,它們才會不遺余力地幫助我們��。倘是它們有個三長兩短����,身體出了狀況,我們的拉沙任務還咋能繼續(xù)��?
我們深知�,在此時此地,至少在拉沙子這件事上����,驢和人是一種辨證的統(tǒng)一。二者互為條件,缺一不可���。沒有驢��,平車就會失去動力�����;沒有人�,平車就會失去方向���。動力和方向��,都統(tǒng)一于平車之上,須臾不可偏廢����。
可見,驢的地位不容小覷�����,驢才是我們當下的第一生產(chǎn)力���!
于是���,回到宿營地����,我們把切草作為了首要任務�����。
不僅切�,還得把草切得碎一點,把草篩得凈一點����,把草上得勤一點。
我們從房頂上扔下幾捆干草來��,大家輪流上手����。沉重的鍘刀,只有使出吃奶的勁兒�����,才能將擩進去的一擼子干草一刀兩斷。當然����,這種營生,除了用蠻力�����,還得使巧勁���。有的人技藝嫻熟�,會在鍘刀提到最高處的一剎那��,渾身一躍����,雙腳離地,懸于空中��,然后隨著身體的回落����,將重力一并用在了鍘刀上��,直切得刀光閃爍、虎嘯生風�、塵土飛揚、草屑亂濺�。這是一種事半功倍的技術(shù),可惜沒有多少人能掌握��。我天生愚笨�����,屢試屢敗��,所以大家都不指望我去提刀�,而是讓我跪在鍘刀的一側(cè),扮演擩草的角色���。擩草雖然不算很累�����,但需要全神貫注�����,倘若三心二意�,離開了掌刀人的節(jié)奏,極有可能把手指頭切掉�。我這個人做事比較專注,所以至今十個手指頭還全部健在����。
我們往往是邊切草,邊把驢喂上����。
等草切下了一大堆,估摸著夠一天吃了�����,方才結(jié)束鍘草的營生���。
再等一會兒�,估計驢肚子里已經(jīng)有了足夠的底墊��,我們才解開韁繩��,把驢牽到院子中央���,放幾桶剛擔回來的涼瑩瑩的井水�,讓它們喝一個痛快淋漓�����。我們管這個環(huán)節(jié)叫作飲驢���。
飲驢也有講究�����,因為驢是不能喝空槽水(空腹水)的���,喝了極易生病,所以先吃后喝�,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和不容倒置的程序。
一天的簡單勞動過后���,大家都休息去了����,我又開始了馬鳴宏書記說的那種在相同時間內(nèi)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價值的復雜勞動�����。
我風風火火地跑到連部,等領導們給了我一些素材后�,走進會議室正式鋪展開了我所承諾過的新聞寫作。
那間會議室�,空空蕩蕩,只有我和一個并不明亮而又時不時地會忽閃幾下的電燈泡相互對視著���。我就坐在那天馬鳴宏書記講話的位置��,它依舊懸掛在房頂?shù)闹醒?���。它俯視我��,我仰望它����,俯仰之間,送走一個又一個疲勞的夜晚��。
我來了����,燈亮了;我走了��,燈滅了。我們配合得非常默契���。

我之所以每天選擇在連部會議室里寫作,絕不是想在領導們面前顯擺什么�����,而實在是迫不得已�����。你想����,宿舍里五個人一鋪大炕,睡前紅起黑倒���,睡后鼾聲如雷����,又無桌椅板凳可供使用�����,這等環(huán)境咋好舞文弄墨?
晚上十點鐘�,我會準時把燈拉滅。因為我不是機器�,我需要通過睡覺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因為我不是正式記者���,明天還得重復今天這樣的復雜勞動加簡單勞動���!因為我不是村里的主要領導,不能像其他帶隊那樣只當指揮員而不當戰(zhàn)斗員�����!因為我不是普通的民工���,喂好驢再喂好自己就可以蒙頭大睡�!因為我不是國家干部��,明天絕不會有人給我放假���!
我只是我自己�����。在特定的環(huán)境里����,只能無條件地去服從自己內(nèi)心的調(diào)遺。
從連部回宿舍���,是一天中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發(fā)愁的一件事情��。
舊寨這地方的人好養(yǎng)狗而又不善管理����,所以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有成群結(jié)伙的狗子們滿街亂竄���。我們宿舍離連部差不多有一里來路�����,又沒有路燈�����,一路上總會遭到狗子們的圍追堵截����,好在我左手拿著一個手電筒,右手提著一根打狗棍��,隨時都可以應對不測��。但那種聲嘶力竭的叫喚和猝不及防的穿越�����,還是會把在黑暗中踽踽獨行的我嚇出一身又一身冷汗����。
我也細心過,想按照馬鳴宏書記的吩咐物色幾個寫手����,以便減輕我們兩個光桿司令的負擔?���?稍L遍連隊,竟無一人納于麾下�����。倒是有人直言不諱地說,不用說寫兩句了��,好歹連半句也憋屈不出來��。此情此景�,令人十分尷尬。
不過�����,這個門面還是硬讓侯新文組長和我這樣的副組長給撐住了�。山道彎連隊在少槍沒子彈的情況下��,新聞宣傳不僅沒有落伍����,在團部每周一次通報的排名中竟然頻繁沖入第一方陣。
馬鳴宏書記除了好為人師好給人講點馬列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工作要求極高���,甚至高到了嚴苛的地步。所以要叫他夸下屬一個好字,那可真是比要命還難的事情����。
可是,在大會戰(zhàn)期間�,他就正經(jīng)八百地表揚了我們宣傳小組以及我這個泥腿子通訊員好幾回。侯新文說馬鳴宏太破例了����,我則說馬鳴宏太破費了。我倆一陣好笑��。
奧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一個人的生命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在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碌碌無為而羞愧��?���!蔽蚁?��,不論將來什么時候���,回想起1977年的大會戰(zhàn)�����,我都不應該有什么悔恨和羞愧了�,因為在那個激情燃燒歲月里�,大會戰(zhàn)的天空回蕩過我稚氣未脫的文章,指揮部的快報飄灑過我青春年少的墨香����,宛若巨蟒的大渠凝結(jié)進了我熱血沸騰的詩行。

徐茂斌
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山西省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趙樹理文學獎獲得者。原忻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忻州市文化局局長����。著有《山道彎彎》《徐萬族人》《黃河岸邊的歌王》(合著)等文學作品�?����!饵S河岸邊的歌王》(被收入《中國新世紀寫實文學經(jīng)典》(2000——2014珍藏版)�。
(責任編輯:盧相汀)